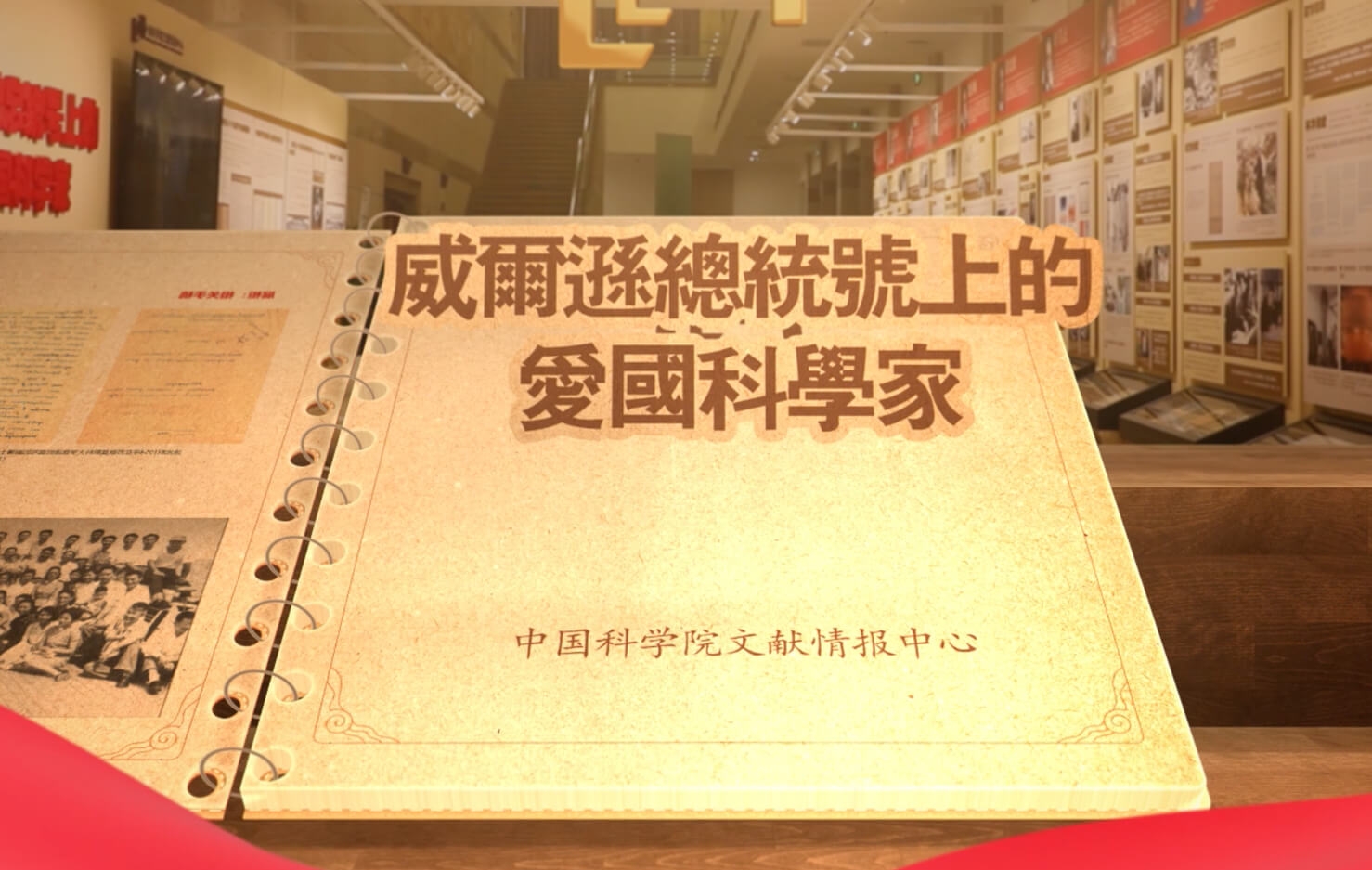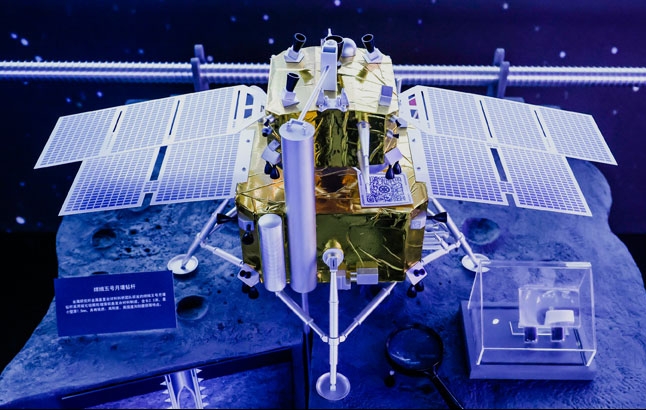陈能宽和亲密战友于敏院士(左)
陈能宽(1923.05.13-2016.5.27), 金属物理学、材料科学、工程物理学家。生于湖南慈利。1946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1948年、1950年先后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顾问和研究员、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汀豪斯公司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实验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和院科技委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兼职副主任等。长期从事金属物理和材料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中,领导组织了核装置爆轰物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组织并参加了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及核装置有关起爆方案的研究等。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等,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科技创新 为国为民】
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物理作业,是一个需要基础理论与具体应用紧密结合的系统工程。当原子弹计划进行到1960年时,理论准备已经有了一定突破,而验证理论所必需的试验进行得并不顺利。我国急需通过爆轰物理实验,对原子弹理论方案加以验证。
1960年6月,37岁的陈能宽由中央选调到二机部北京九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担任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当时邓稼先明确地对陈能宽说:“我现有的认识、参数和计算工具都无法单靠理论来解决至为关键的爆轰设计。你来了就好了,请你从实验途径来解决吧。”这也是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的共同看法。然而,在1960年,我国学术界在爆轰物理方面的实践经验和学术沉积还接近于空白。
原子弹产生核爆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枪法”,一种是“内爆法”。“枪法”结构简单,威力小,美国在广岛投掷的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就采用这种方法;“内爆法”结构比较复杂,但威力更大,而且更适合原子弹武器化的需要。为了保证原子弹研制成功的可能性,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组织者决定两条腿走路:“把比较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同时进行‘枪法’的理论计算”。但是,人们最大的希望还是寄托在更高级的“内爆法”上面。
“内爆法”要求原子弹组装的常规炸药产生均匀的内向爆炸力,在以微秒(百万分之一秒)计的计时精度内精确聚集到裂变物质的表面,使裂变物质瞬时内达到或超过临界值。同时,爆轰所产生的高温高压使金属变成第四态的等离子体,释放出大量的中子进入裂变芯。要攻克“内爆法”,除理论上需解决一系列难题外,在试验方面也有两个“拦路虎”。一个是炸药的组装形式,一个是点火装置。陈能宽带领的爆轰实验室的任务,就是通过试验来设计炸药的装配方式。
陈能宽带领团队从“零”做起,仅用两年时间就手工造出上千枚炸药部件,做了上千次试验,初步建立起核武器爆轰物理理论和试验体系,完成了相关设计和测量研究工作,并带动了炸药以及光、电测试的技术攻关。
之后,在陈能宽和王淦昌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大型爆轰试验节节突破,为原子弹、氢弹突破奠定了重要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随后,空投核航弹和导弹核武器先后试验成功,原子弹实现武器化,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在我国核武器加紧攻关的时候,超级大国为保持核优势,以其达到的技术水平设置门槛和限制,于1963年签署了“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妄图把中国核武器扼杀在摇篮里。如何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测试技术,成为摆在攻关人员面前的新挑战。
陈能宽和朱光亚、王淦昌一起提早筹谋,并亲自参与大部分核试验的方案制定和组织领导,带领团队攻克了面临的测试技术难题,使试验方式实现了从空爆、地爆向地下平洞和竖井试验的转变,试验的效费比也大大提高。
之后,又成功完成了从全当量到减当量的试验,打破了“限当量核试验条约”的限制,再一次粉碎了超级大国的图谋。
对于中国核武器人而言,“争气弹”的成功只是辉煌的起步。此后数十年间,以陈能宽为代表的科学家们转战草原、戈壁、大漠、深山,默默无闻、艰苦卓绝地探索世界尖端科技,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核武器科技事业发展道路。
1996年全面禁核试验以后,核武器及其科学技术发展进入到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由于布置、掌握了先进的科学实验方法,我们具备了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进行较量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画册:技术科学部分册[上] [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2.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物理学卷 (2)[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3.刘仓理,陈海波. 陈能宽的创新启示[N]. 光明日报,2016-08-18.
4.宋健主编. “两弹一星”元勋传[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